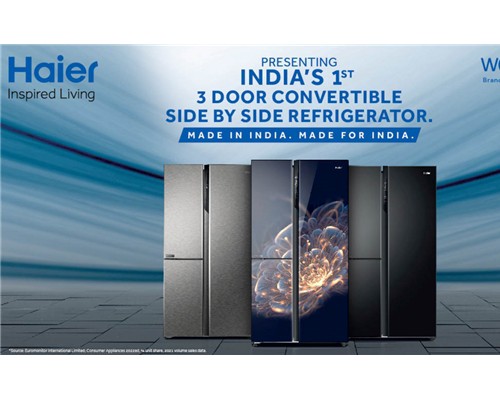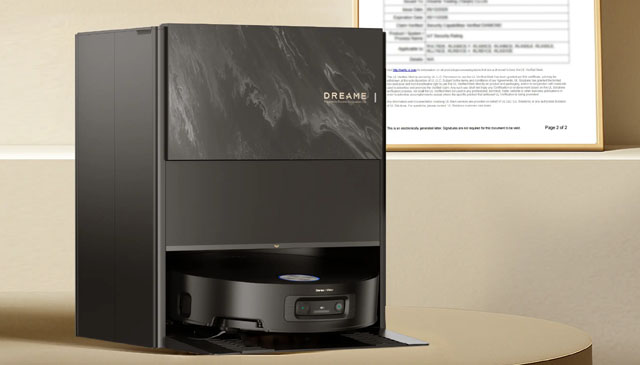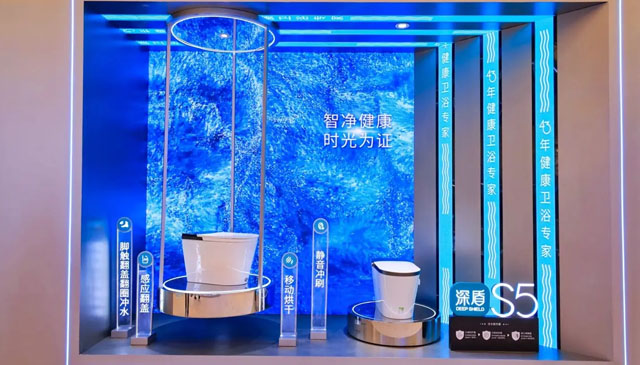芯片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总投资300亿人民币的紫光南京半导体产业基地和总投资300亿人民币的子港国际城项目正式开工。这是紫光集团继长江存储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动作”。据报道,紫光南京半导体产业基地项目由紫光集团投资建设,主要产品为3D-NAND Flash、DRAM存储芯片,占地面积为1500亩。其中项目一期投资约100亿美元,月产芯片10万片。。
但外媒对这一动作感到疑惑。因为从他们早前的分析看来,就算是武汉新芯项目,似乎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来支持存储芯片制造。紫光这次想通过南京的项目来主导全球存储产业,似乎并不能一蹴而就,当中还需要有很多的障碍需要跨越。首当其冲的就是有经验的存储芯片工程师的缺乏和美国CFIUS因所谓的安全问题将中国拒之门外。
而根据新浪科技早期的报道,赵伟国在月前的一个庆典上说到:“在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在武汉打造了一个存储基地。进入2017,我们将会在南京和成都再建设两个半导体制造基地。这三个项目的总投资总额将超过700亿美金,清华紫光在未来将主导芯片制造业”。
分析师认为,紫光集团的这个投资速度是非常惊人,但他们也指出,建设一个晶圆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而需要面临的则是运营问题,尤其是在制造更复杂的3D NAND Flash上,紫光集团面对的困难也是空前的。
对半导体有深入研究,并写过基本关于日本半导体发展的书的作者Takashi Yunogami曾经对武汉新芯的3D NAND Flash项目有些许怀疑。但最近他改变了看法,他告诉我们,从材料和设备供应商与中国的合作中他能看出,或许会有新的转机。
那么究竟中国建设存储项目需要面对那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来一一分析。
工程师短缺
Yunogami表示,中国正在全球掀起一场对有天赋工程师和制造NAND Flash设备的争端战。而同样的事情也在中国本土发生,不同的省市也在掀起了Fab工厂合作的竞争。
在分析中国存储制造技术相关方面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中国有哪些正在崛起的存储供应商。
在IC Insights副总裁Brian Matas早期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存储领域有三个主要的竞争者,分别是:
(1)2016年7月,紫光集团收购了武汉新芯,并建立了一个叫长江存储的合资公司。这个12寸晶圆厂将聚焦在3D NAND Flash的生产,至于具体的量产时间,还没有披露。
(2)合肥SKT项目,预估在2017年底建造一个DRMA FAB;
(3)福建晋华项目,准备打造DRAM Fab,预估在2018年第三季度量产;
而据我们得知,在以上三个项目中,合肥的SKT项目已经停止运营了。这个由尔必达前CEO Yukio Sakamoto建立的公司,曾经尝试从日本、台湾和韩国招募1000个存储相关的工程师,以弥补中国在有经验的存储开发工程师的不足,Sakamoto更是想从日本寻找180个能够迁到中国来工作的工程师,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合肥当地政府的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满足Sakamoto提出的,给这些资深工程师多付887,000美元工资。
尽管SKT的承诺超过了半导体行业的正常现象,但这也给了中国半导体人一些新的方向。一个能够笼络工程师去保持他们Fab继续运行的方法。
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有个工程师跟我们说,中国不但需要考虑专利短缺的问题,中国更需要明晰隐藏在专利背后的制造诀窍。甚至连怎么安排wafer的的存储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例如这些经验并不能通过获得,而要通过不懈的学习。
而在设备方面,长江存储方面表示,他们现在用的半导体设备和三星在西安工厂所使用的是一样的(三星的西安工厂只制造32层的NAND Flash,64层的NAND Flash是在韩国本土制造)。Yunogami也认同这种观点。
但Yunogami进一步指出,虽然长江存储能买到同样的设备,但他们缺少有经验的人去操作这些设备。
总有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纵观存储产业的发展历史,中国可以向韩国学习,而这也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认为,对于长江存储来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从三星西安这些公司挖角晶圆厂操作工人。之后可以从三星和SK海力士挖一些高级的工程师。再看能够从美光和东芝获取一些相关的技术信息。这是紫光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根据Yunogami介绍,韩国存储以前在追赶日本DRAM的时候,用过同样的方法。
是个世纪90年代,三星花费重金从日本招聘DRAM工程师。当时那些工程师可以保留白天的工作,而可以在晚上或者周末为三星服务。通过这些兼职工作,工程师们能获得高额的报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三星逐渐发展其了其DRAM产业。
而二十多年后的今日,韩国受到了当初日本的对待。虽然中国并没有韩国当初那么疯狂,但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组织长江存储招聘来自西安三星的工程师。
相关进展
据之前的报道,长江存储计划斥资240亿美元打造一个12寸的晶圆厂,第一期工程在2016年底就开启了,并计划在2019年完成。而报道中更是指出,长江存储的产能高达20万片每个月,而主要的生产产品则是32层的NAND FLASH。
长江存储武汉基地的建设布板
Yunogami坚信长江存储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这主要是通过深度研究Spansion的Mirror-Bit技术实现的(最早是为Nor设计的,但后来三星将其应用到NAND上)。而长江存储在去年底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3D NAND Flash测试。根据Yunogami所说,第一次测试是在12月中完成的,但当时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之后的第二次测试的产品则可以执行全规格的运行。但至于具体的进展如何,我们也实在不得而知。
相关的任务标语
谈谈钱的问题
老实说,在中国追逐存储国产化的国产中,有一件事是我不能了解的。那就是既然长江存储正在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为什么紫光集团那么急切地在另一个地方投资了下一个工厂。这个决定出乎了很多国外专家乃至中国本土专家的所料。
在文中开头我们提到,紫光集团和南京政府达成了一个合作。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紫光集团更是计划在四川程度建一座逻辑工艺的晶圆厂,而这家厂的预估产能是50万片一个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紫光集团去疯狂的建厂?
中国三大存储基地
美国的资深半导体老兵对中国这个存储布局的评价是——这令我们很头疼。
从中国现在资金投入来看,基本上是中央放出来一笔基金,然后各地的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开始介入,然后三方通力合作,打造半导体产业链。而在这些合作中,不同城市和省份之间也会竞争,谁都想成为最先成功的一个。
美国的相关分析师认为,长江存储的武汉项目并没有预期中的进展那么好,政府方面有所怨言,因此紫光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所以紫光需要从其他城市寻求帮助。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TSMC在去年三月也和南京政府签订了一个12寸晶圆建厂协议。专家们指出,TSMC虽然表现得和南京政府和左右很大热情,但在工厂规模上,并没有达到南京政府的需求。为了被武汉击败,所以南京政府选择和紫光集团合作。
可能面临的风险
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半导体建设最终会引致一个结局,那就是产能过剩。
去年,IC Insights的Matas写到,现在在追逐3D NAND Flash的产能的公司有三星、SK海力士、美光、英特尔、东芝/闪迪和长江存储。还有一些可能加入战局的中国制造商。
Matas表示,未来3D NAND将会面临各方面的风险。
虽然业界认为未来五年工业界会发生很重要的转变,并会带来很强大的存储需求,但如果中国的存储布局能够顺利进行,那么最后必将会面对差能过剩的风险。
有人指出,对于中国的这些投资我们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究竟是应该感谢他们致力于打破三星的垄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还是该批判他们这种行为?
这位专家海指出,中国想通过存储切入半导体产业链,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存储上面投资的金额实在太大了。每一代技术的投资成本都数十亿美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投资无数的钱在一个未知结果的领域,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展开全部许多对电脑知识略知一二的朋友大多会知道 CPU 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晶体管了,提高 CPU 的速度,最重要的一点说白了就是如何在相同的CPU面积里面放进去更加多的晶体管。
由于 CPU 实在太小,太精密,里面组成了数目相当多的晶体管,所以人手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笑),只能够通过光刻工艺来进行加工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块 CPU 里面为什么可以数量如此之多的晶体管。
晶体管其实就是一个双位的开关:即开和关。如果您回忆起基本计算的时代,那就是一台计算机需要进行工作的全部。两种选择,开和关,对于机器来说即0和1。
那么如何制作一个CPU 呢? 以下我们用英特尔为例子告诉大家。
首先:取出一张利用激光器刚刚从类似干香肠一样的硅柱上切割下来的硅片,它的直径约为 20cm。除了 CPU 之外,英特尔还可以在每一硅片上制作数百个微处理器。每一个微处理器都不足一平方厘米。 接着就是硅片镀膜了。相信学过化学的朋友都知道硅(Si)这个绝佳的半导体材料,它可以电脑里面最最重要的元素啊!在硅片表面增加一层由我们的老朋友二氧化硅(SiO2)构成的绝缘层。这是通过 CPU 能够导电的基础。
其次就轮到光刻胶了,在硅片上面增加了二氧化硅之后,随后在其上镀上一种称为“光刻胶”的材料。这种材料在经过紫外线照射后会变软、变粘。然后就是光刻掩膜,在我们考虑制造工艺前很久,就早有一非常聪明的美国人在脑子里面设计出了 CPU,并且想尽方法使其按他们的设计意图工作。CPU 电路设计的照相掩膜贴放在光刻胶的上方。照相字后自然要曝光“冲晒”了,我们将于是将掩膜和硅片曝光于紫外线。这就象是放大机中的一张底片。该掩膜允许光线照射到硅片上的某区域而不能照射到另一区域,这就形成了该设计的潜在映像。
一切都办妥了之后,就要到相当重要的刻蚀工艺出场了。我们采用一种溶液将光线照射后完全变软变粘的光刻胶“块”除去,这就露出了其下的二氧化硅。本工艺的最后部分是除去曝露的二氧化硅以及残余的光刻胶。对每层电路都要重复该光刻掩膜和刻蚀工艺,这得由所生产的 CPU 的复杂程度来确定。尽管所有这些听起来象来自“星球大战”的高科技,但刻蚀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工艺。几个世纪以前,该工艺最初是被艺术家们用来在纸上、纺织品上甚至在树木上创作精彩绘画的。在微处理器的生产过程中,该照相刻蚀工艺可以依照电路图形刻蚀成导电细条,其厚度比人的一根头发丝还细许多倍。
接下来就是掺杂工艺。现在我们从硅片上已曝露的区域开始,首先倒入一化学离子混合液中。这一工艺改变掺杂区的导电方式,使得每个晶体管可以通、断、或携带数据。将此工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以制成该 CPU 的许多层。不同层可通过开启窗口联接起来。电子以高达 400MHz 或更高的速度在不同的层面间流上流下,窗口是通过使用掩膜重复掩膜、刻蚀步骤开启的。窗口开启后就可以填充他们了。窗口中填充的是种最普通的金属-铝。终于接近尾声了,我们把完工的晶体管接入自动测试设备中,这个设备每秒可作一万次检测,以确保它能正常工作。在通过所有的测试后必须将其封入一个陶瓷的或塑料的封壳中,这样它就可以很容易地装在一块电路板上了。
目前,英特尔已经量产10nm芯片,7nm芯片还在研发之中。尽管微处理器的基本原料是沙子(提炼硅),但工厂内空气中的一粒灰尘就可能毁掉成千上万的芯片。因此生产 CPU 的环境需非常干净。事实上,工厂中生产芯片的超净化室比医院内的手术室还要洁净1万倍。“一级”的超净化室最为洁净,每平方英尺只有一粒灰尘。为达到如此一个无菌的环境而采用的技术多令人难以置信。在每一个超净化室里,空气每分钟要彻底更换一次。空气从天花板压入,从地板吸出。净化室内部的气压稍高于外部气压。这样,如果净化室中出现裂缝,那么内部的洁净空气也会通过裂缝溜走-防止受污染的空气流入。
但这只是事情一半。在芯片制造厂里,Intel 有上千名员工。他们都穿着特殊的称为“兔装”的工作服。兔装是由一种特殊的非棉绒、抗静电纤维制成的,它可以防止灰尘、脏物和其它污染损坏生产中的计算机芯片。这兔装有适合每一个人的各种尺寸以及一系列颜色,甚至于白色。员工可以将兔装穿在在普通衣服的外面,但必须经过含有 54 个单独步骤的严格着装程序。而且每一次进入和离开超净化室都必须重复这个程序。因此,进入净化室之后就会停留一阵。在制造车间里,英特尔的技术专家们切割硅片,并准备印刻电路模板等一系列复杂程序。这个步骤将硅片变成了一个半导体,它可以象晶体管一样有打开和关闭两种状态。
这些打开和关闭的状态对应于数字电码。把成千上万个晶体管集成在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上,能表示成千上万个电码,这样您的电脑就能处理一些非常复杂的软件公式了。
整理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