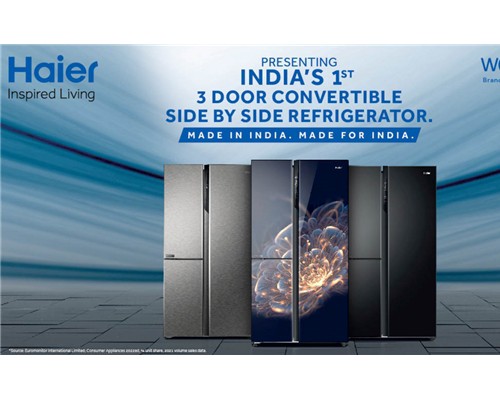恐怖袭击为何瞄上法国
马晓霖++陈季冰
2015年11月13日晚,西方文明的心脏地带巴黎遭受了自“9·11”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已造成132人遇难,352人受伤。
14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对这次巴黎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声明还宣称,法国将依然是“伊斯兰国”今后攻击的主要目标。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宣布法国全境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唯一的核动力航母开赴中东打击“伊斯兰国(ISIS)”。
其实,单单就解决ISIS这个任务而言,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件太大的难事——ISIS的能力并不比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更强。问题出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而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严重对立,并被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离间和利用,则是恐怖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的根源所在。
为什么又是法国?
这已是法国在一年内连续遭受的第二次严重恐怖袭击了。今年初,同样发生在巴黎《查理周刊》编辑部及其他多地的连环袭击事件曾造成17人身亡;今年8月,在一列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往法国巴黎的高速列车上,若不是有两名正好在欧洲休假的美军士兵挺身而出,一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AK-47自动步枪也许已经让上百乘客横尸当场……
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首要目标,主要原因就在于恐怖主义的这种内生化:法国是最踊跃地跟随美国一起打击中东极端组织——包括ISIS——的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法国也是欧洲穆斯林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比例最高的国家,在法国总共5000多万人口中,穆斯林人口超过500万。法国本身还是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欧洲人数最多的国家,迄今已有超过1500名法国穆斯林作为圣战者为ISIS或者其他暴恐组织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已经返回法国……
从近年来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圣战者袭击”——例如波士顿马拉松赛(2013年4月)、伦敦街头(2013年5月)、渥太华战争纪念碑(2014年10月)和悉尼酒吧(2014年12月)——都是由所谓“独狼恐怖分子”策动的。这些凶残的杀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自己袭击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其中很多甚至出生在西方国家。
这其中既有文化冲突,也有经济原因。
在巴黎,不同种族间的分割,是比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区隔”更沉重的话题。如果9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著的《区隔》只讲了工人和精英间的趣味场,那如今不同民族间的隔阂更是在地域上体现。法国人、非裔、亚裔、穆斯林分布在不同的区,标榜着不同的高低之分,也暗含着不同的治安水平。
欧洲穆斯林的高失业率——在许多国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宗教,也包括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
美国的世界教俗地位与定位
世界历史上下几千年,无论纵向缕析还是横向扫描,能延续千年且依然对世界政治和人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文明: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以中东为腹地的伊斯兰文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
中华文明的持续辉煌始于秦汉,臻于唐宋,明代中叶转入衰退。伊斯兰文明发轫于7世纪,即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勃兴与传播,最终形成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地域的信仰共同体,甚至将辉煌的波斯和古埃及都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并在中世纪融汇为登峰造极的伊斯兰文明,而且又被奥斯曼土耳其加以延续和光大,直到大航海时代开始没落。
自文艺复兴至21世纪中叶五六百年间,西方文明重新崛起且一统天下,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双双跌落衰败的低谷。近三十多年,古老的中国开始复兴,生机勃发。但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依然无望再次中兴。
二战导致欧洲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横空出世。无论是联合国机制,还是美元货币体系,乃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美国领军设计的全球架构。
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从总统到议长公开宣称本国是世界“领导者”。美国历届总统,无论党派如何,都自觉承担一种所谓使命,即在全球推广美国的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凡是与美国模式不同的,基本都被列为独裁或非民主国家。
同时,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文化打底的国家。历任总统大都来自基督教不同派别,从总统到国务卿宣誓,几无例外手摸《圣经》,宣誓效忠上帝和美国,也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及其人民。美国不少总统宗教情结相当浓厚,特别是布什父子,其所有公开演讲充斥着宗教语汇,如罪、恶、善、宽容、主等等。
所以,在美国政治家眼里,非民主、非基督徒国家,与基督教关系不好的政权,也都是要收拾的对象。“9·11”袭击发生伊始,小布什曾口无遮拦地说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尽管后来为此道歉,但他本能的表现和内心所想已是路人皆知。
美国及其欧洲小伙伴战后几十年努力颠覆的政权,基本来自两大方向:社会主义阵营,所谓“铁幕”国家,如前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缅甸;还有一类,是伊斯兰世界那些不听美国指挥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
西方在伊斯兰世界长期树敌
1947年是美国重装进入中东的初年。经过两次大战的消耗,英法意等传统中东殖民宗主国已无力维持统治,冷战阵营逐步形成,美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应运而生。这三大事态紧紧地将美国与中东捆绑在一起,也自然开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睦的时代大幕。
当年另一影响中东格局的重大事件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81号决议,将奥斯曼帝国遗产巴勒斯坦一分为二,打开中东“潘多拉魔盒”。次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结束,犹太人的以色列如期成立,“阿拉伯国”却因众多阿拉伯统治者抵制安理会决议而流产。
阿拉伯人认为,祖先留下的土地,为何割给只占人口1/3的犹太人一多半?犹太人自被罗马镇压驱离后,已有1000多年不再是巴勒斯坦主体民族,伊斯兰世界为何要给西方的排犹屠犹恶行赎罪?但是,巴勒斯坦分治是大国政治博弈的结果,不平的种子就此埋进阿拉伯人的土地,也埋进穆斯林的心田。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看来,以色列完全是在美国一手呵护下成立的,以色列宣布独立仅7分钟,美国就率先外交承认,甚至其独立宣言中的某些关键句子,还是杜鲁门总统亲自修改定调。
首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击溃5个阿拉伯国家的攻势,加剧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此后历次阿以战争,除苏伊士运河之战外,美国全都旗帜鲜明地为以色列保驾护航,并否决几十个不利于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草案。
美国将自己和西方绑在以色列的战车上,逐步酝酿和发酵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反西方情绪。生于官宦和高知家庭的“基地”组织第二任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就是在阿以冲突的挫败感中逐步变成仇视美国、西方及其“傀儡政权”的激进分子,直至最终走向恐怖主义。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主义的追随者颠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占领美国使馆的示威者缴获大量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策动政变并图谋颠覆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证据。反美反西方声音迅速地成为这个并非阿拉伯民族、又信奉什叶派教义的穆斯林社会的主旋律。
此后,伊拉克和伊朗爆发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巴格达,与萨达姆商谈美国援助。整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概况为“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推动埃及跟以色列实现单独媾和,拆分和削弱阿拉伯和伊斯兰反以阵营;联合西方伙伴以各种手段和方式,维持两伊战场处于僵持和均衡态势,使伊斯兰世界两强陷入长期内耗。
美国的地区政策,再次激起和加深对美国和西方的愤懑,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实施了第一起针对美法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数百美法海军陆战队员死亡。此后,针对美国和西方目标的绑架、劫持、袭击在中东一度层出不穷。
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老布什应科威特和沙特王室邀请,并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于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解放科威特,打垮萨达姆军队,随后启动马德里中东和会,首次整体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撮合一处,共谋和平,美国在中东的影响也如日中天。
但是,此后美国驻军常态化和机制化,和平进程又朝着更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这两大因素使得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反美情绪重新抬头,并引发富二代本·拉登与美国反目,筹建“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十字军国际联盟”——“基地”组织,直至2001年发动“9·11”袭击,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全面开战。
两场战争加剧文明对立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十几年时间过去,美国和西方盟友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更加糟糕,加剧既有的文明分歧和对立。
首先,十几亿穆斯林关心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人的公平与正义悬而未决。美国曾高度关注的中东和平进程,在小布什后期基本被弃之脑后,奥巴马当政后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巴勒斯坦问题几乎完全被边缘化,美国的中心只有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而这两个战场,包括与阿富汗毗邻的巴基斯坦,直接和间接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无辜百姓死亡。在激进的穆斯林看来,这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欠下的又一笔文明血债。
其次,美国和西方军队、保安公司对战乱地区伊斯兰信仰、文化和传统的蹂躏屡见不鲜。无论是黑水人员在伊拉克的大开杀戒,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残暴虐囚;无论是北约军人在阿富汗玷污和焚烧《古兰经》,还是玩弄塔利班士兵尸体甚至撒尿作践,更不用说无人飞机频繁误杀平民,都激起一波波抗议与仇恨。实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的肇事者之一就曾声称,他因为目击阿布·格莱布虐囚恶行,才开始仇恨美国和西方。
即使在美国国内,以琼斯牧师等为代表的极端基督教分子,也在借助焚烧《古兰经》,不断挑动与伊斯兰群体的冲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穆斯林战俘或犯人,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和非人待遇,经媒体曝光后直接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陡增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恶感,也必然激化双方从文化、宗教和心理方面的抵触和敌视。
俯瞰伊斯兰的文化傲慢与自大
电影是传播文化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好莱坞大片是西方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的有效载体,也是妖魔化伊斯兰的重要手段。据统计,自1896年电影问世至2000年间,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仅12部基调是正面的,其他要么反映伊斯兰世界的愚昧、落后和保守,要么描述穆斯林是色情狂或恐怖分子。当然,随着不同时代政治话题和热点地区的变迁,被侮辱的穆斯林角色也会出现变化。
知名大片《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里,施瓦辛格主演的硬汉,就是与一群阿拉伯恐怖分子和色鬼做斗争的英雄,坏蛋们对白直接用阿拉伯语狂呼乱叫。类似情节在有关伊斯兰题材的影片中相当常见。
2011年美籍导演库奈·巴赛利粗制滥造的所谓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则延续好莱坞强暴伊斯兰情感的卑劣传统,创新了抹黑、羞辱穆罕默德的艺术形式,进而引发波及世界的抗议浪潮,并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斯蒂文森等三名外交官的遇难。
其实,此前的《查理周刊》事件,只不过是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撒旦诗篇》的漫画版。那部惊世骇俗的辱教作品,因严重突破公认禁忌,冒犯穆斯林宗教情感而导致几十个国家的持续抗议。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因此颁布宗教法令,要求全世界穆斯林追杀拉什迪,并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引发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直接摩擦与对立。
然而,欧洲的知识界、艺术界并未汲取历史教训,也可以说,依然漠视穆斯林的质朴情感,重蹈拉什迪覆辙,导致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与冲突接连不断。